世界气象组织在今年公开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平均温度已较工业化之前的水平上升了1.1℃,如果不考虑2016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升温效应,那么2019年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热的年份。
去年底参加完在西班牙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我当时最深的感受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的分歧依然很大,尤其在减排责任划分和绿色气候基金分摊机制等方面,这种周而复始的争论很可能会让我们错过最佳的温升控制的时间窗口。
全球气候变化并不像雾霾等局地空气污染那样易于被人即时感知。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还要不要参与全球减排?从人类共同福祉来说,当然应该积极参与,但从自身发展状况来讲,还是要清楚地了解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包括不同的产业和区域层面,这应该最终决定我们参与的强度和投入的力度。
过去几年,我的课题组一直在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发现,1℃平均温度的升高将使国家层面的经济产出下降0.86%,据此估算,过去20多年里,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2400亿美元。
而全球气候谈判能否达成实质性成果在于可感知的气候损害和大多数国家的态度,而一国能否提出合理的减排方案,争取到公平的排放权,考量的依然是国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实力。当前在全球尺度上对各国气候变化影响测度和排放控制政策评估,采用的主要技术是综合评估模型(IAM),相关的研究成果一直支撑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平均每5年一轮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报告,这一技术在谈判桌上的分量因而也是不言而喻的。
从2010年关注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开始,我们就意识到了模型实力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何历时多年也要坚持和团队成员自主开发综合评估模型的原因。自主模型开发是一项耗时且风险很高的研究工作,我们不仅要面临起步晚的天然劣势,还不得不错过很多发表文章的机会,而开发的模型如果创新性不足还极难得到国际模型界的承认。
当时,我们实际上是发现了主流模型体系的两个明显缺陷后才决定开始工作的,一是绝大多数综合评估模型对能源技术的刻画不足,其自顶向下的建模框架不允许大规模能源技术的考虑,而后者恰恰是测度减排影响,描绘低碳转型路径的关键。我们借鉴生态学中种群扩散的机理,提出了一种新的多重能源技术演替机制。这种方法理论上允许我们引入无穷多种能源技术,并巧妙地刻画能源系统与经济系统和气候系统间的动态交互作用,从而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综合评估模型的局限。二是现存模型对技术进步的研究存在不足,这可能导致技术正效应的低估,继而高估应对气候挑战的成本,降低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我们发展了多因素技术学习曲线,在基础综合评估模型框架内同时考虑了内生和外生两种技术进步机制,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尽管未来在模型进一步发展和深层次应用上还面临诸多挑战,但以后发者跻身先进模型的行列已属不易。
可喜的是,近些年国家对这一领域的支持力度很大,也有越来越多的团队加入模型技术的开发中,但在当前的环境下要克服后发劣势,发展出一批先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模型还面临较大的挑战:首先是要有连续的资金支持和稳定的研发团队,欧美一些代表性的模型团队往往历经十年二十年,依然在坚持创新和维更,这是做一项大工作最难能可贵的。其次,对这些基础性研究要弱化论文发表的重要性,因为模型开发是一项十分耗时的工作,期间几年甚至多年都难以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我们要提供“坐冷板凳”的环境和“允许试错”的机制。最后,加强国内合作以及与国际先进团队的交流。经过数年的发展,综合评估模型体系已日趋完善,要再有根本性创新是很困难的,从支撑国际谈判,服务减排战略的角度看,我们需要的是有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产权模型体系和国际话语权,这显然不是单打独斗可以实现的。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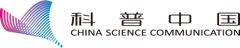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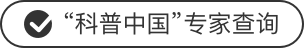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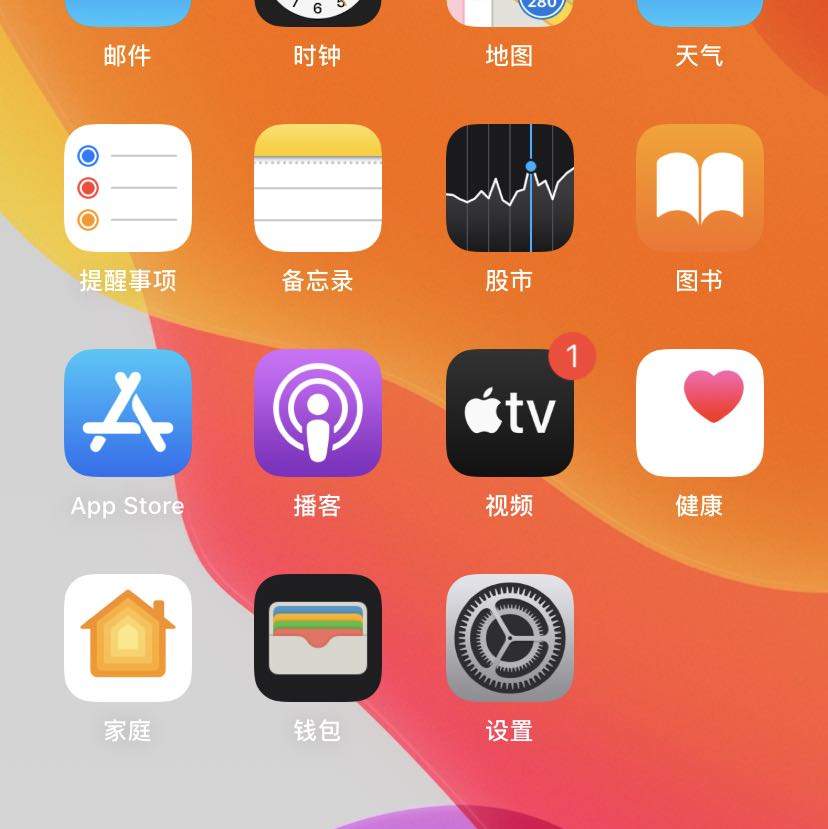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