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公众号:艺旅文化授权发布
李倕冠饰复原 陕西西安唐李倕墓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图源:文博圈
金铜打底,银丝塑形,绿松石、红宝石、琥珀、珍珠、玛瑙、贝壳……几乎所有类型的宝石,都在这件头冠上拥有一席之地,色彩绚烂,极尽奢华。
这是李倕墓中出土的公主冠冕。唐代女子头冠能够完整流传下来的本就不多,这么精致完整的就显得尤为珍贵。
李倕冠饰初步处理后
但是,它刚出土的时候,可完全不是这样。
由于埋藏的时间太久,出土时冠冕连带头骨被泥土包裹,在土壤的重压下,冠冕的层层材质缠绕在一起,甚至难以分辨每个部件应该在的位置。
李倕墓出土复原冠饰(局部) 图源:文博圈
文物修复专家通过激光定位等手段,历时两年时间,才终于让这尊冠冕恢复昔日的精致。
这件公主冠,是最近的热门展览《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中的一件展品。
此外,还有秦始皇帝陵出土彩绘兵马俑、韩休墓壁画、战国船棺葬出土漆床等文物也依次亮相,向我们展示着我国如今文物保护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彩绘紫衣御手俑 通过新材料的研发与使用,陶俑上的彩色涂料才得以保留 图源:文博圈
01.
什么是文物修复?
作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先辈为我们留下了数量浩瀚的文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珍贵的文物难免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害。如何对文物进行修复,自然是考古人和文博人十分关注的领域。
《我在故宫修文物》中,负责钟表类文物修复的王津老师
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类别不同,文物的修复方法不同。即使是同一大类下的不同小类,也有截然不同的修复方式。
在保证文物价值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修复人员要遵循如下原则:
最小干预性和可逆性的原则,灵活运用科学的保护措施,做到保持文物原貌,修旧如旧。同时,在保护的时候也要注意预防,杜绝“保护性损害”。
石膏是陶瓷修复中常用的修补材料,性质稳定,易于塑形。
一件石膏修补的宋代黑釉盏 图源:浙江新闻
在材料方面,首先要保证修复所用的材料对文物本身不能有伤害,像一些具有腐蚀性的胶水之类,基本上是不能使用的。
除此之外,文物修复的材料要具有“可逆性”,如果将来有更好的材料,或者是修复水平有进步的时候,还能重新进行修复。
揭去命纸后给画心上浆 图源:知乎@SME情报员
文物种类五花八门,修复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瓷器粘结、青铜焊接等等等等,就不多做赘述了。
兵马俑(面部) 图源:文博圈
这次展览中展出的文物,都是在最新科技成果的指导下修复而成,代表着我国文物修复的最高水准。但是,受限于文物修复相关知识科普不到位、人手不足等情况,文物保护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02.
刷上热搜的“毁容式”修复
曾经,有许多堪称“毁容式”修复的文物刷上热搜,不过这些文物有很多是民间团体自发性的修复。尽管是出于好心,却由于不够专业,为文物的未来增添了许多不确定的色彩。
资中东岩 拈花笑佛像 曾被收录进《中国美术全集》
比如,这尊位于四川内江资中东岩的佛像。它开凿于南宋时期,一龛两像,一佛一弟子,佛是释迦牟尼,赤足立于莲台上,右手拈花,脸含笑容,略向前倾,俯视左下壁的弟子迦叶,构成一幅独一无二的拈花微笑图,在中国石窟艺术中十分罕见。
当地的信众或许是觉得这尊佛像过于朴素,突然决定要为佛祖塑一尊金身,于是,它,成为了一尊“咖喱味”的佛。
又或许是因为效果实在是“让人目不忍视”,这尊佛像又被二次妆彩,这次,它变成了这样。

这类事件不止发生在我国,国外也有不少文物,因为当地居民的“好心”,而遭受了“无妄之灾”。
《戴荆冠耶稣》是收藏在西班牙东北部小镇教堂的一幅壁画,由西班牙19世纪著名画家埃利加斯·马丁内斯所绘,由于其画笔细腻,人物传神,多年来一直被当地居民视为无价之宝。
由于小镇气候潮湿,《戴荆冠耶稣》上的颜料局部脱落,显露出斑斑白迹。可这是一幅歌颂主的油画,怎么能放任它腐朽下去呢?
于是,一位好心的老奶奶“来不及通知”教堂和文物保护部门,悄悄买来了颜料和画笔,趁着“月黑风高”夜,亲自动手开始了“修复”工作。
心是好心,只是能力上实在是欠缺了几分。原作中耶稣的面部笔触细腻,如今却变成了“四不像”。眼神呆板,嘴巴糊成一团,脸部更是整个变形。
尽管专家们在发现后紧急修复,但至今,这幅画像也未能恢复原貌。
清代云接寺壁画修复前后对比,责令整改后,这里现在是一片白墙
面对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修复结果,我们总是“好笑又好气”:一面为这些文物感到不值,一面又对那些迄今为止没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文物们感到担忧。
03.
可识别还是修旧如旧
——文物修复原则的矛盾
除了专业度不够之外,文物究竟怎么修,修成什么样,也是这些年来国际上一直讨论的问题。
一般来说,国外向来倡导文物修复的可识别性原则,即文物修复的部分和文物本身有着明显的区分。在这样的原则下,既可以对文物进行修复,也可以保证后来者对文物的理解不会受到修补者的影响。
听起来非常完美,只是在实行中,又遇见了另一个问题——“有点”不好看。
马德雷拉古堡
就如这座位于西班牙西南部城市卡迪兹的马德雷拉古堡,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矗立了千年。1985年西班牙政府还将它列为文化遗产,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近百年来,虽然没有外力介入,但大自然侵蚀这一关也不是好过的。仅剩断瓦颓垣的马德雷拉古堡,如今砖石脱落,岌岌可危。
西班牙政府一看,不能再继续放任了,急忙找人来修复古堡。只是……

这座时间和战争都没有摧毁的古建筑,于2017年,在工人们的“鬼斧神工”之下,成功地由古堡“升级”成为“碉堡”。
不过,虽然丑了点,但还是能很明显看出西方在文物修复中坚守的可识别性原则——修复补充的部分均是采用白色标出,十分显眼。
帕特农神庙 图源:昵图网
相比之下,希腊人对帕特农神庙的修复,可识别性的成果就柔和多了。
目前,国内也会采取类似的手段。对于出土数量众多的陶瓷器,专家们也会采用白色石膏,将修复处和其他部分区别开来。
河南郑州博物馆中的陶器,白色石膏部分是后来修补的
不过,相对国外来说,国内的文物界对于文物的态度还是以“修旧如旧”为主,争取将残碎的文物做到完全看不出修复的痕迹。
比如,突逢大难成为碎片的文物,是这样修复的;
商青铜鼎 出土时碎成了47片 修复者:刘胄 来源《了不起的匠人》
有许多著名的青铜器文物都属于此类。
清宫旧藏班簋碎成小片,在垃圾场等待进入熔炉时被专家认出,后经补兑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完好无损”的样子;
四羊方尊被炸成20多片,也被专家巧手修复。如今看来,几乎难以寻觅修补的痕迹。
修复中的四羊方尊 历史图片
而面对那些完全看不出原貌的文物也是这样。
五牛图
只不过,与国外的可识别性相似,这种修复方式也有瑕疵。根据材料记载还原出的文物,还是有微小的可能会出现的缺漏。而且,这些失误一旦出现,便很难被识别出来。
04.
“旧”与“旧”
鬼斧神工一般的修复技术之下,又衍生出一个新的问题:
你说的“旧”是什么“旧”?
是修成文物最原本的样子吗?
造阁前的千手观音
重庆大足石刻群中有一尊千手观音像,88平方米的崖面上,830只手、眼错落排列,形态各异,状如孔雀开屏。因此,这尊集雕塑、彩绘、贴金于一体的佛造像,被称为“人间一绝”。
由于追求旅游效益,当地景区在塑像周围建造了封闭的特龛参观点。千手观音造像在川渝地区湿热的气候环境被迫下盖了三年“被子”,终于得了“皮肤病”——塑像上的金箔层开始大片大片的脱落。
造阁后的千手观音 局部 图源:知乎@刹
造阁后的千手观音 面部 图源:知乎@刹那
为了修补这尊造像,专家们花了八年时间,潜心研究。
他们既分析了这座诞生在南宋的造像在历朝历代的反复妆彩中使用的材料,又对造像上已经腐化的部分做清理和防腐。只是,在佛像修补完毕再次展出的时候,还是收到了一片骂声。
或许百年前金箔脱落掉色前,这尊佛像确实是这个样子
“失去了古意”、“土豪审美”……类似的声音不绝于耳,可这一次,专家团可是“有苦说不出”。无论是从修复前的考察结果,还是从在修复过程中意外的考古发现来看,用金箔修复佛像都是正确的决定。
全新的金箔既能保护胎体不被风化侵蚀,延长佛像的保存时间,又符合佛教造像的贴金传统,延续传承了传统的贴金装彩工艺。
因为“太新了”被骂,未免有些委屈。
那么,注意度,不追求完好,就让它保持着第一次见到它的样子可以吗?
对于大部分保护状况良好的文物来说,专家们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总有一些文物“病入膏肓”,让它们保持这种状态,算得上是百害而无一益。
《赵城金藏》刚被发现
《赵城金藏》是宋代我国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开宝藏》的复刻本,即玄奘自天竺取回的梵文经卷中译善本,对我国佛教历史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
令人难过的是,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书卷受潮发霉,在抢运的过程中又被藏在一个废弃的煤矿矿井中,粘上了很多粉尘,几乎成为了一根“碳棒”。
修复后,至少可以阅读其中的内容了 经过整整十六年的修复,先蒸再揭,一页一页细细地裁接,慢慢地将“一根碳棒”还原成一卷经书。 这才有了我们如今啧啧惊叹、学术界如获至宝的《赵城金藏》。
修复前后对比图
从上面的种种示例来看,就不难理解这些年,有关“文物究竟修成什么样才合适”这个话题的争论不休了。
纵然有国际法则里,《威尼斯宪章》对于文物修复范围的明确界定,又有之后《奈良真实性文件》中,对于文物的真实性原则进行的重新定义。但是,受限于各个国家的国情,这些文件也很难得到贯彻实施。
在没有明确规定的当下,也只能根据修复者和对文物的实际需求,来决定这个微妙的度了。
文物修复 图源:光明网
除此之外,文物修复工作人员严重不足也是个大问题。据2019年的数据显示,全国文物系统3000多万件馆藏文物中,半数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
而我国真正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人员,全国也不过2000人。以每人每月修复1件文物计算,仅修复博物馆内现有的破损文物,至少也需要上千年。许多博物馆里甚至没有专业文物修复人员。
纵然这几年来,随着文物热的到来,文物修复工作者的数量有了微量的增长,但仍然是杯水车薪。
近几年来,文物修复到底该怎么修的讨论一直是热点。更有甚者,对于文物要不要修这件事都产生了怀疑。
知乎截图
无论是直面风霜的石窟壁画,还是收藏室里妥善保管的金银玉器,这些文物跨越千百年的时光来到我们面前,带来的除了悠远的古韵,还有历史刻下的累累伤痕。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对于破损的文物,无论是出于研究意义还是收藏价值,都是应该修复的。只是,现在的文物修复与保护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相信未来有一天,在这次《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中提及的高新科技的加持下,可以弥补现在的缺憾,而那些以修复为名的破坏,将不再出现!
看到这样的修复,连盗走小耶稣头的小偷都无法忍受,归还了头颅
🕳
互动话题
#文物修复应该留下修复痕迹,
还是修旧如旧呢?#
欢迎在留言中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哦~
人文\艺术\行走
有温度的文化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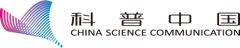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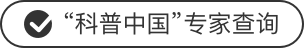


 扫码下载APP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